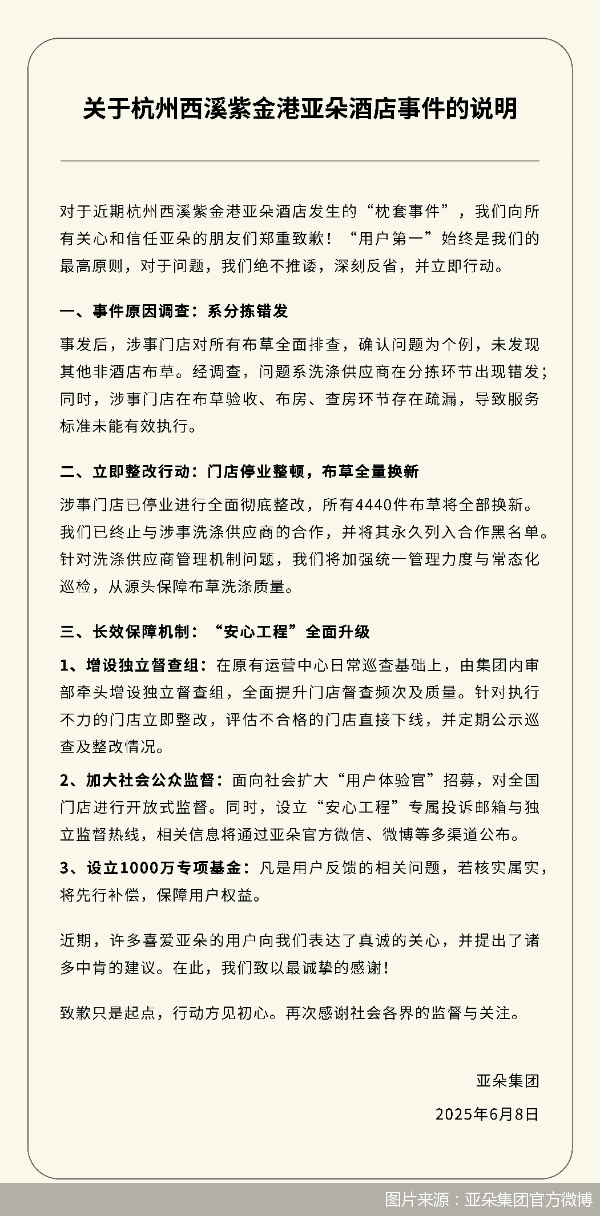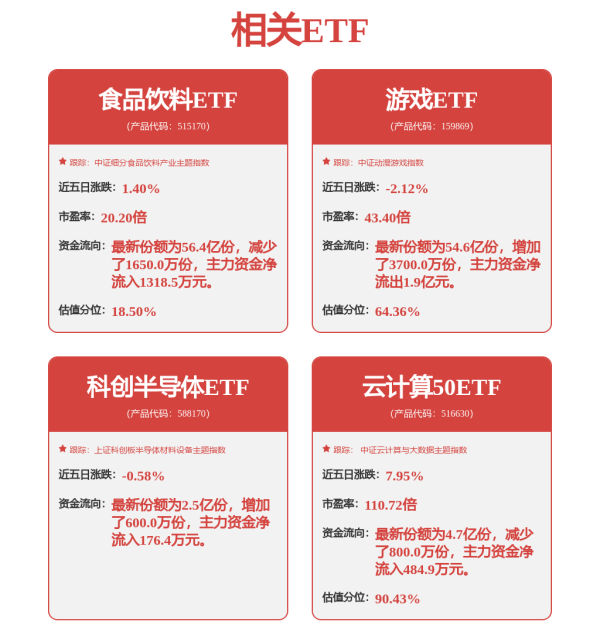文|徐 来科元网
编辑|徐 来
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1976年夏季,一架军用直升机意外撞上山体,机上中将与其亲生儿子当场罹难。
这起事故背后,围绕着一个沉甸甸的问题——国家究竟给他们家发放了多少抚恤金?
1976年7月7日,福建东南沿海天空阴沉,云层厚重。
中午时分,一架军用直升机从漳州军用机场起飞,飞向东山岛。
这次飞行任务并不复杂,是部队的常规勘察,行程紧凑,安排匆忙。机上共有十三名乘员,除飞行员外,乘客身份各不相同,但最受关注的当属皮定钧中将。
展开剩余87%皮定钧年过六旬,身为正军级将领,是新中国建国时首批授衔的中将之一,后任福州军区司令员。
他没有选择坐指挥车,而是带着儿子皮国宏,一同登上这架直升机。
此次飞行既非战时紧急任务,也非紧急调动增援,而是一次普通的军事巡查。
当天上午,天气预报并不理想,东南沿海低压系统盘旋,夹带着海雾。
原本应慎重考虑天气状况,评估是否适合飞行,但飞机仍按计划起飞。机体穿梭在厚重云层中,导航设备较为有限,飞行员只能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目测来判断航向。
接近中午十一点时,地面雷达突然失去飞机信号,十几分钟后,军区警报响起。
有人听见一声巨响科元网,赶到现场,只见一片焦黑的残骸,直升机撞上了漳浦县灶山的山体,整架飞机断为两截,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。
那一刻,没有任何生还的奇迹。皮定钧和儿子坐在机舱中部,座位被机体残骸卡住,根本无从逃脱。
机上十三人名单中,多是年轻军官,还有两名机组成员。
尸体辨认工作直到傍晚才结束,有的尸体只剩半截军装,有的面容因火烧而模糊不清。
军方随后发布了简短公告,未透露事故细节,仅称“执行公务时遭遇空难”。
当时全国正处于特殊政治时期,事故处理非常低调,报纸上几乎没有详细报道,只有简短的通稿。
内部调查结论并不复杂,归因于恶劣天气和导航失误。这一切都被封存在档案袋里,成为机密编号。
皮定钧出身红军老战士,安徽金寨人,15岁便加入红军,随队走完长征。
抗战时期曾参加黄河抗战、守卫陕北。建国后,逐步升任军区司令,性格直率,讲话带着浓厚的皖西口音,在军中享有良好人缘。
1970年代,皮定钧调任福州军区,负责东南沿海防线。
他带兵严谨,常年深入基层,极少携家属随行。
皮国宏是家中长子,自幼随父军旅生活辗转各地,后来考入军校,毕业后转业至地方机关工作。
此次随父同行,既无正式公文,也未有调任命令,纯属私人意愿。有人猜测他想看看部队状况,也有说法称父子久别重逢,正好搭上这趟飞机。
皮国宏年仅28岁,新婚不久,妻子在厦门工作。事故当日,家人尚在单位焦急打听父子行踪。
下午收到军区通知时,家属泣不成声,连夜赶赴漳浦,只剩下一副沾满血迹的皮带作为身份标识。
烈士评定手续迅速完成科元网。
皮定钧按“因公殉职”处理,列入军队重大伤亡档案;皮国宏虽未正式服役,但鉴于同行性质,也被追认为烈士。
军中不少战友默默焚香祈福,有人写下长信投入墓地角落,有人感慨:“他一生带兵,最后却牵连了儿子。”
那几天,福州军区多次降半旗悼念,军医学校主动出力协助遗体处理和运送。
这对父子就这样静静地被送走,声势极为低调。
随后,关于抚恤金的讨论悄然展开。
消息传回家属院时,皮家门前已围满人群,却无人开口。张烽站在门口,手握毛巾,神色平静无波。
那年她刚过五十,突然成了寡妇,也成了烈士母亲。
单位迅速安排慰问,军区政治部送来了两封盖红印章的讣告。
副司令亲自前来吊唁,带来一只搪瓷水杯、一条毛巾和一只牛皮纸袋,纸袋并不厚,里面装的就是抚恤金。
根据当年军队因公殉职的规定,皮定钧的抚恤金一次性定额补助为500元。
虽军衔为中将,且属于特殊事故,有人期待金额会有所增加,但并无附加。张烽接过钞票,仔细数了数,确实是五张崭新的百元大钞,边角叠得整齐。
儿子未服现役,虽追认为烈士,抚恤金由福建省民政厅发放,最终到账金额仅两百多元。
两笔钱加起来,不到八百元。
张烽未曾言语,将钱存入银行,账户名称写为“家庭专用”。
几个月后,她在一本旧账本上记下几笔花销:1976年10月购布两匹,做了一件新棉衣,花费18元;1976年12月回金寨祭祖,路费23元。
之后再无记录。有人说她变得节俭,有人说她从此不再提丈夫。
那年物价不高,一斤大米约三毛多,5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四年工资。但对皮家来说,这500元并非奖赏,也不是荣耀,而是一条突如其来的终点线。
战友们曾提议为皮定钧立碑,张烽拒绝:“他生前连照片都不爱挂,活得踏实,死也别张扬。”
1979年,全国开始调整抚恤政策,张烽收到军区来信,告知抚恤金标准过低,将补发差额款。她未多言,仅点头同意。
几个月后,补贴款到账,连利息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元。
她默默将钱再次存入银行,这回改用“专项用途”账户,没人问她打算,她也未透露。
1982年,她取出存折,带着身份证和介绍信,前往福州鼓楼一处写着“儿童福利基金会”的办公室。
填写资料后,将存折与现金全部捐出。
捐款人栏里,只写了“烈属张烽”。
她未向部队透露此事,也未告知子女,只是静静地将丈夫和儿子的抚恤金,含本金与利息全部捐赠出去。
多年后,一位基金会老员工谈起此事,称:“她的眼神很平静,毫无自我牺牲的表情。”
她从未在家提及这笔钱的去向。有人劝她买电暖器过冬,她摇头说:“家里够暖。”此后无人再提。
直到她去世后,子女整理遗物时,才在一张泛黄的文件袋中发现捐赠收据。
金额是¥1,062.35元,印章清晰,落款为“福建省儿童福利基金会”。
这是一段发生在三十年前的故事。
如今,谁还记得,那笔钱,是一个中将和他的儿子在空难中换来的。
那年飞机碎了,人散了科元网,抚恤金只剩一张收据,承载着未曾言说的遗愿。
发布于:天津市升富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